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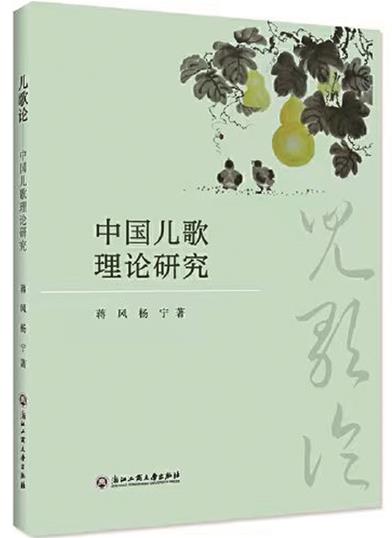
□ 汪胜
儿歌作为幼儿最初接触的文学体裁,以其浓厚的趣味性吸引着每一位孩童。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理论家蒋风就着手开启了儿歌的收集和研究,并于1977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儿歌浅谈》一书,该书是蒋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特殊环境里的产物。
2020年,蒋风和学生杨宁合著的《儿歌论:中国儿歌理论研究》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实际上是《儿歌浅谈》的修订本,该书从儿歌的缘起到当代的发展脉络做了详细的梳理与总结,并从儿歌的概念、特征、功能、表现内容、表现手法、修辞、儿歌教学,以及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进行了细致详尽地阐述。
儿歌的历史
儿歌存在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世界各地,当文学尚处于口耳相传的阶段时,儿歌就出现了。古时候儿歌属于民间文学中民间歌谣的一种,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而成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儿歌以口头创作、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流传,由于其口头性的特点,有不少儿歌散佚在历史的洪流中。文字的出现以及文人的搜集、整理、记录使我们今天得以在诗书典籍中了解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古代儿歌。
明代吕坤所编《演小儿语》是我国第一部古代儿歌集。他收集了流传在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地的46首儿歌,并将其编撰成书。这些儿歌文字浅显,内容生动活泼。如《打哇哇》:“打哇哇,止儿声,越打越不停。你若歇了手,他也止了口。”吕坤当时出于“训蒙之用”对很多歌谣进行了修改,并在每一首儿歌下面加了评语。尽管如此,《演小儿语》“利用儿童的歌词,能够趣味与教训并重,确是不可多得的”。最重要的是,《演小儿语》使后世的人们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了解古代儿歌的概貌,也使古代的一些儿歌得以保存。
清代郑旭旦所编撰的《天籁集》成书于康熙初年,郑旭旦在书中最早提出儿歌是“天籁”的说法:“天机活泼,时时发现于童谣。”书中收集吴越地区儿歌48首。一类是反映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的,这类儿歌既有成人创作的,也有儿童随口编唱的。这类儿歌有的用于游戏,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的类似于绕口令,锻炼儿童的思维和语言,如“一颗星,挂油瓶;油瓶漏,炒黑豆”。还有的具有一定的道德教育意义。另一类则是表现成人的生活,主要由成人创作向儿童传唱,儿童虽然不懂儿歌的内涵,但音律上的节奏感往往使儿童乐于接受并传诵。
继《天籁集》之后,清代悟痴生共收集吴越儿歌23首编撰成《广天籁集》,因其内容和形式都与《天籁集》相似,所以人们常常把这两本儿歌集相提并论。例如钟敬文先生在《民间文学概论》中提到,“清代郑旭旦的《天籁集》和悟痴生的《广天籁集》中,记载了近七十首儿歌,为我们保存了极宝贵的古代儿歌资料”。
儿歌作为一种现代术语被广泛应用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了现代阶段,在大量搜集整理和出版传统儿歌的基础上,创作儿歌开始出现了,作家们本着“儿童本位”的意识为儿童创作儿歌,儿歌进入了自觉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新老儿童文学作家们以自己创作的艺术劳动,开创了新中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儿歌创作也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出现了大量优秀的创作儿歌,如鲁兵的《太阳公公起得早》《山羊》《小猫》《纺织娘》,陈伯吹的《摇篮曲》,圣野的《都是好孩子》《扮老公公》《奶奶故事多》《乘凉》,金波的《一列火车长又长》《野牵牛》《大老哥》《云》,刘饶民的《种葵花》《赶鸭》《什么多》,金近的《数字歌》《大西瓜》,等等。这一时期的儿歌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形式也多样化。从内容上看,鲁兵的《太阳公公起得早》、圣野的《都是好孩子》、金波的《一列火车长又长》等强调对儿童的教育,张秋生的《插秧歌》、刘饶民的《种葵花》、圣野的《奶奶故事多》《扮老公公》、金波的《大老哥》《云》等更多地表现了儿童的趣味和心理。从形式上看,陈伯吹的《摇篮曲》是摇篮曲的形式,金波的《野牵牛》是连锁调的形式,刘饶民的《什么多》是问答歌的形式,金近的《数字歌》是数字歌的形式。可见,无论是数量、内容还是形式,这一时期的儿歌创作都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高峰时期。此后,中国儿歌创作一直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看,都涌现了不少优秀作品。
改革开放使儿歌发展迎来了春天。“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幼儿文学蓬勃兴起,各种幼儿文学报刊的创办,众多儿歌集的出版,都对儿歌的创作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更为可喜的是,这一时期的儿歌创作在继承儿歌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审美化和低幼化方面做出了努力,如金波创作的《雨铃铛》:“沙沙响,沙沙响,春雨洒在房檐上,房檐上挂水珠儿,那样圆,那样亮,好像串串小铃铛!丁零当啷……丁零当啷……它在招呼小燕子,快快回来盖新房!”儿歌以丰富的想象力,把挂在房檐上的水珠想象成晶莹剔透的雨铃铛,美好的想象营造出一幅优美的画面。这样的儿歌创作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很多,中国当代儿歌发展也不断走向繁荣,老中青三代诗人以自己的辛勤创作为儿歌的繁荣默默耕耘着。
儿歌也是诗
蒋风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拓荒者之一,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开始,他就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教学、研究之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蒋风着手开启儿歌的收集和研究,并于1977年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儿歌浅谈》一书,该书是蒋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特殊环境里的产物。此后,蒋风一直致力于在低幼儿童中推广儿歌,在他看来,儿歌也是诗。
儿歌是儿童文学中的一种类型,作为文学作品,其根本的性质显然是文学性。儿歌的语言虽然简短,但同样带给儿童读者审美的体验。世界各国都非常注重儿歌的发展,1976年3月21日,在比利时召开的一次国际诗歌会议上,聚集了一批令人尊敬的关心孩子、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的诗人,为了“关心儿童、缔造和平、消灭战争、建设家园”的宗旨,他们倡导在全球创建一个特殊的节日——世界儿歌日。
蒋风说,儿歌能让孩子们获得最早的精神陶冶和知识启蒙。他回忆自己年幼时在妈妈怀抱里度过的那些温馨岁月,儿歌带着天籁般的情愫走进他的感情世界,至今,他仍然时常会想起母亲在他小时候的轻声吟唱:“一颗星,咯咯叮;两颗星,挂油瓶;油瓶漏,好炒豆;豆子香,好种秧……”轻快、委婉的旋律,给童年蒋风带来无穷乐趣。
离休后,蒋风全身心投入儿童文学的推广活动,致力于在海内外提倡童诗教育。有一年,浙江师范大学幼儿园准备开展童诗教育找他商议时,蒋风很赞成并表示愿意尽最大力量参与。幼儿园开展童诗教学是一件极具创新意义的事,只不过要从实验对象的特点出发,幼儿园的童诗教育要以儿歌为主。儿歌也是诗,儿歌比儿童诗更贴近婴幼儿生活。
儿歌是歌,“歌咏言”,音乐性一般比儿童诗要强。它大多押韵,朗朗上口,且词汇浅显,易唱易记。它的内容大多是快乐的,配合游戏,边玩边唱。它是一种歌谣体的诗。
儿童诗是诗,“诗言志”,它着重表达儿童对生活的感觉和理解。儿童诗的内容要比儿歌更宽泛一点,感情更丰富细腻一些。儿童诗也讲究音乐性,但它的音乐性体现在诗的内在节奏,诗作者的情感波动决定诗的节奏和韵律。它抒发的感情,不仅有快乐的,也可能有忧伤的、悲愤的;不仅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追求,也抒发对某些生活现象的困惑和思考。它的句式、长短、押韵与否,不受限制,且语言往往带一定的书面色彩。它是诗,属于自由体的诗。它追求意象的创造和情感的妥帖传达。儿歌和童诗都是儿童诗歌,两者虽有些区别,但没有绝对的界限,且常常相互交融,有的儿童诗常呈现儿歌化,儿歌也常会诗化。
因此,儿歌也是诗,尤其是优秀的儿歌往往都蕴含着浓浓的诗味。如陈伯吹的《摇篮曲》。这是一首地地道道可以唱的儿歌。“风不吹,浪不高,小小的船儿轻轻摇,小宝宝啊要睡觉;风不吹,树不摇,小鸟不飞也不叫,小宝宝啊快睡觉;风不吹,云不飘,蓝蓝的天空静悄悄,小宝宝啊,好好地睡一觉。”这是一首艺术性极高的儿歌。作者用十分优美而口语化的文字,唱出一种静悄悄、甜蜜蜜的意境。“风不吹”“浪不高”“树不摇”“云不飘”“小鸟不飞也不叫”……一个个意象,营造了一个安详恬静的梦境,童趣盎然。
有一位诗人曾说:“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像婴儿一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发现世界的新的美。”有一次,蒋风在幼儿园听见中班的孩子在唱《小鼓响咚咚》:“我的小鼓响咚咚/我说话儿它都懂/我说小鼓响三声/我的小鼓咚咚咚//哎哟,小鼓这不行/妹妹睡在小床中/我说小鼓别响了/小鼓就说懂懂懂。”
这是一首朗朗上口的儿歌,小鼓的响声“咚咚咚”,与人说的“懂懂懂”是一对贴切的摹声词,而且把主人公关心他人的感情非常准确地表现出来。正是这种极富幼儿特点的情感,使这首儿歌诗意葱茏。
发自内心的诗是真正的诗,发自内心的歌也是真正的诗。具有诗情画意的儿歌才能引起幼儿的共鸣,才能赢得孩子的喜爱。因此,儿歌也是诗。
修订完善
《儿歌论:中国儿歌理论研究》
晚年,蒋风一直想修订完善《儿歌浅谈》。几年前,蒋风的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杨宁来看望他,闲聊中,蒋风偶然谈起修订完善《儿歌浅谈》这件事,杨宁很感兴趣,当即表示愿意结合她的教学科研工作共同参与书稿的修订。
修订之前,蒋风挤出时间做了两项工作:一是起草了一份详细的修改提纲,二是整理了收藏的相关资料。正当杨宁满腔热情进行这项工作时,她又刚好被她所在的赣南师范大学派去美国访学一年,她怕因此影响书稿修订进度,把顾虑告诉蒋风,蒋风却觉得,去美国访学不但不影响书稿修订进度,而且刚好可以利用在美国访学找到更丰富的资料,修订好“中外儿歌比较”等章节,提高书稿质量。
修订过程中,杨宁又因对“儿歌理论发展系谱”缺乏研究、缺少资料找到蒋风,蒋风马上想到了自己的忘年交——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潘颂德教授。
潘颂德在五四以来包括儿歌在内的新诗理论方面造诣很深,出版过两部新诗理论巨著:《中国现代诗论 40 家》(重庆出版社 1991 年版)和《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学林出版社 2002 年版)。前者由臧克家写序,并得到高度评价:“他的文艺观点比较正确,不随风乱转,不以今日的目光强求于前人。他对每位诗论家,不管成就大小,就论而论之……这种就事论事、讲道理的态度是很可取的。”后者在学术界也得到充分的肯定:“史料翔实,论从文出……占有资料的丰富性、新颖性和运用史料的准确性令人惊叹。”
如此权威的专家,蒋风想邀请他一起执笔修订书稿相关部分的内容,潘颂德满口应允。但是,潘颂德学术活动繁忙,未能按时完成,等他完稿,书稿已经排版待印。因此,潘颂德的诗论作为附录列入书后。
2020年,蒋风和杨宁合著的《儿歌论:中国儿歌理论研究》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蒋风这一沉在心里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儿歌论:中国儿歌理论研究》从儿歌的缘起到当代的发展脉络做了详细的梳理与总结,并从儿歌的概念、特征、功能、表现内容、表现手法、修辞、儿歌教学,以及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角度进行了细致详尽的阐述。同时,该书引用大量诗作举例分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读者沉浸在儿歌带来的艺术美感里,重温起一种久违的童心、童趣、童乐,让人身心突然涌上轻松愉快之感。因为,这些儿歌都曾是我们童年时光里不可或缺的快乐源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附录部分列出的潘颂德的诗论,除了对周作人、刘半农、朱自清、鲁迅、褚东郊、钟敬文、鲁兵、圣野、张继楼、金波等作了生平简介外,还重点对他们的儿歌诗论观点予以了详细、深入地加以阐述和说明,让读者更深入了解和掌握了一些关于儿歌方面的历史知识和创作的重要性。
文中谈到周作人时说道:周作人很早就重视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周作人从幼儿的生理、心理和学习语言的特点的角度说明儿童在儿童发育、成长上的重要性。周作人继续研究儿歌,不但深化了上述他的《儿歌之研究》的儿歌理论,也为五四时期的儿歌理论研究做出了他个人的独特贡献。
谈到刘半农时说道:刘半农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包括儿歌在内的民间歌谣。刘半农之所以高度肯定民间歌谣,是因为歌谣的语言、声调及所抒发的感情都具有自然、真挚的特点。刘半农认为传统儿歌的声调可以借鉴利用。
谈到朱自清时说道:朱自清充分肯定了儿歌的教育意义。朱自清关于儿歌教育作用的论述,启示我们必须努力创作富有人文精神的儿歌,引导儿童传唱富有教育意义的儿歌,让广大儿童在传唱优秀儿歌中健康成长。
谈到鲁迅时说道:鲁迅很早对儿歌产生兴趣,对包括儿歌在内的歌谣有深入的研究。鲁迅认为,儿童文学作品“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以孩子为本位”,就是要在熟悉少年儿童生理、心理、思想、感情、知识水平特点的基础上,针对三四岁的幼儿到十四、十五的少年儿童在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想象、思维、语言、感情和意志等心理方面的特点,来创作适合少年儿童年龄特征,包括儿歌在内的儿童文学。同时,鲁迅还十分重视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认为写给少年儿童看的文学作品,要通俗易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总结了我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优良传统和发展规律以及总结了五四以来新诗创作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就新诗的形式如何实现民族化、大众化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谈到褚东郊时说道:褚东郊从儿童年龄特点角度揭示儿歌的地方性、口授性。褚东郊认为儿童的知识有限,儿歌为容易唤起儿童的兴趣起见,歌中所引用的事物,往往必须就儿童日常耳目所接触的着想。这样,儿歌歌唱时,才“格外觉得亲切有味”,所以“儿歌中含有极浓厚的地方色彩”。
谈到钟敬文时说道:歌谣,20世纪20年代普遍分作民歌与儿歌两大类。钟敬文指出,当将民歌与儿歌对举时,“应包含一切流行于民间的歌在内”的民歌,其含义相当于“成人的歌”。
谈到鲁兵时说道:鲁兵认为儿歌是人生最初的蜜,给幼儿创作的儿歌,要符合他们的年龄特征。还认为:“有些儿歌给孩子一些事物的概念,看起来杂乱无章,其实也是有些联系的,给孩子一些日常生活知识和地理概念。”
谈到圣野时说道:圣野形象地说“儿歌是逗人的,能把哭娃娃逗笑,没有半点家长的威严,没有任何粗暴的训诫,孩子们是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教育内容的”。圣野精辟地指出儿歌的美化作用是与儿歌的德育、智育作用融汇在一起产生作用的,他还揭示了儿歌美育内涵的两个方面:一是“优秀的儿歌,总是反映美好的事物,创造美妙的世界”,二是儿歌独具的“特别强烈的音乐性”。圣野关于儿歌形式的观点,既符合儿歌形式的艺术辩证法,又科学地总结了当代儿歌形成的现状,对当代儿歌形式的探索具有指导意义。
谈到张继楼时说道:张继楼将儿歌理论奠基于儿童的本能、年龄特征之上。张继楼的儿童文学评论、儿歌评论,非常注意文学评论的辩证法,讲究儿歌评论的科学求实精神。张继楼通过长期的儿歌创作实践,以他的大量儿歌丰富了我国当代儿歌宝库,他的儿歌理论批评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理论观点,不但充实了我国现代儿歌理论体系,还在当代儿歌创作实践中,引人深思,指导广大儿歌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儿歌精品。
谈到金波时说道:金波特别注重与强调儿歌的“儿歌味儿”,他认为儿歌既有实用性,又有“文学性”,二者并不矛盾。金波的儿歌理论,给我国的儿歌理论、儿童文学理论展示了广阔的天地。
这些精辟的论述,对于学习写儿歌、童诗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知识。只要读完、领会一番,真是大受裨益,对写作儿歌大有帮助和启发。《儿歌论:中国儿歌理论研究》也给后人在欣赏、学习、写作儿歌童诗时指明了方向。
儿歌教育的意义
儿童文学的产生和儿童教育是密切相关的。儿歌作为人之初文学,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教育的功能。儿歌的题材十分广泛,涉及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儿歌的主要接受对象是低幼儿童,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在思维水平、接受能力、审美能力等方面都不同于大龄儿童。
因此,尽管随着新课标的颁布,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品进入小学语文教材,但不同体裁的编排在不同年级的所占比重是不同的。儿歌在一二年级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所占篇幅较多,以目前使用率最高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为例,一年级上、下两册教材中,儿歌30篇左右,二年级上、下两册教材中,儿歌8篇左右。这些儿歌编排在教材中的汉语拼音、识字、课文、语文园地等栏目中。
考虑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识字水平、理解能力、接受心理等因素,编者对选入教材的大多数儿歌做了相应的改写,例如刘御的《小白兔》,原文是:“小白兔、穿皮袄,耳朵长来尾巴小。豁豁嘴,胡须翘,一动一动老在笑。”选入教材之后,儿歌做了相应的改写:“小白兔,穿皮袄,耳朵长,尾巴小,三瓣嘴,胡子翘,一动一动总在笑。”原文的排列是两节,进入教材后改为单节,原文第三句是一个长句,进入教材后改为了两个短句,和前两句形成了一致的节奏。从字词上看,原文的“豁豁嘴”改为了“三瓣嘴”,更加浅显形象,易于被儿童接受,“老在笑”改为了“总在笑”,所表达的意思不变,但改动之后语言更通俗易懂。程宏明的《比尾巴》选入教材后也做了改写,其中比较明显的改动是把原文中的“谁的尾巴好像一把扇?”改为“谁的尾巴最好看?”相对应的回答也做了改动,由“孔雀的尾巴好像把扇,”改为“孔雀的尾巴最好看。”这一改动其实削弱了原文表达的形象性,而且从整体上看,和上一节的一问一答“谁的尾巴好像一把伞?”和“松鼠的尾巴好像一把伞。”之间也缺少了一种句式上的呼应。当然,也有一些儿歌进入教材后未做改动,例如叶圣陶的《小小的船》,郑春华的《轻轻地》,寒枫的《菜园里》等。应该说,不管是改写还是不改写,选编者的目的都是使儿歌能够充分发挥作用,以更好地适应小学语文的教学。
在一、二年级的语文教材,尤其是一年级的语文教材中,被编排在不同栏目的儿歌由于栏目的教学侧重点不同,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进行儿歌教学时,可以根据不同栏目的要求,结合儿歌的特点,选取相应的教学方法,例如朗读教学法、赏析教学法、戏剧教学法和习作教学法,儿歌的朗读教学能激发学生的朗读兴趣并提高他们的朗读能力和对儿歌的理解能力;儿歌的赏析教学可以引导学生学会理解、分析、鉴赏儿歌;儿歌的戏剧教学能充分发挥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儿歌的习作教学可以初步培养儿童的写作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儿歌教学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儿歌并掌握相关的知识,充分发挥儿歌的作用,这也是儿歌教育的意义所在。
来源:《今日婺城》(2024-04-25 03:婺江)
编辑:蒋红跃